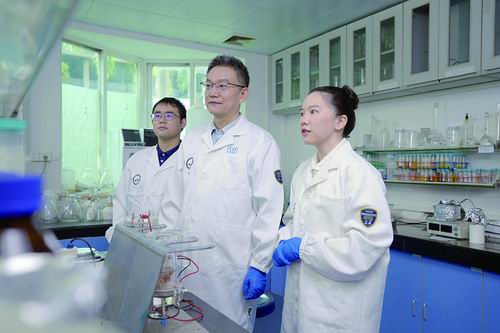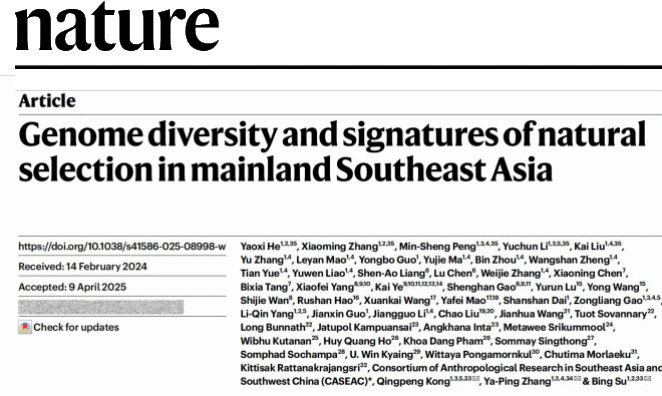李校堃:无行业影响力的高校缺乏“生命力”
■本报记者 高雅丽
一提到温州,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繁荣的小商品经济、繁忙的对外贸易……总之,温州似乎只与“钱”有关,而与“科”少缘。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比如2024年底,在温州市举行的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大健康论坛上,温州正式启动建设“生长因子(FGF)之城”,计划打造bet36备用:乃至全球生长因子研究和产业化的高地。
所谓“生长因子”,简单而言便是一种促进细胞生长的物质。温州之所以将其确定为自身科研发展的重要方向,与温州医科大学这所省属“双非”高校密切相关,更与学校的“掌门人”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密切相关。
2005年,李校堃来到温州。此后20年间,他率领科研团队落地温州,将不被外界看好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做出了名堂。其研发的生长因子药物如今已在近万家医院使用,累计治疗患者一亿多人次。
在他的带动下,温州医科大学在国际“生长因子”创新药物研发领域已占据领先优势,科研实力比肩部分“双一流”院校。学校的“中国基因药谷”和“中国眼谷”两个产业转化平台,成功孵化超过30家医疗器械企业,吸引了200多家企业入驻,甚至把温州这座城市打造成为全国“生长因子”研发和产业的高地。
“一名教授如果对企业没有影响力,一所学校如果对行业没有影响力,便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。”在李校堃看来,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是互动的,一批人能拉动一座城市、一所大学能润养一座城市,必须打破学校的围墙,让教育更加开放、拥抱社会。
30多年投身一件事
《中国科学报》:30多年前,生长因子研究在医学领域属于小众学科,你为什么会投身这个领域?
李校堃:我的一生都与生长因子结缘。我研究生长因子30多年,深知它的潜力和价值。
1992年的一个深夜,还在暨南大学读博的我骑车时不慎摔进一个深沟,导致脸部多处穿透伤,要缝30多针。我很担心会因此“毁容”。那一刻,我突然想到了实验室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。彼时,国际上对生长因子的应用还存在一些质疑,担心它可能会失控导致异常生长,但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,心想如果运气不好,至少也算是为科学做了一次试验。
于是,我朝脸上喷了些动物实验阶段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喷剂。没想到第二天,我的伤口就开始结痂,3周后痊愈,没有留下一点疤痕。这次经历让我坚信这种药物在临床应用上有广阔前景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研发新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需要面对质疑和不解,你为何会坚持下来?
李校堃:我也有孤独、无助、彷徨的时刻,但从未想过放弃。我心里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——外国人不做,中国人就不做了吗?中国的科研不能跟着别人走。我们通过近30年的持续研究和大量临床试验,用国际认可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中国研制的“生长因子类”药物是安全、有效的。
1998年,我们团队研发的重组牛bFGF(贝复济)获一类新药证书并上市,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将“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”家族开发为临床药物的国家,上市时间比日本早4年、比美国早6年。2002年,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hFGF(扶济复)获一类新药证书并上市。2006年,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haFGF(艾夫吉夫)获一类新药证书并上市。
同时,生长因子适应证从过去单一针对烧烫伤,延伸到糖尿病、溃疡等难愈性创面,以及角膜溃疡、宫颈糜烂、脊髓损伤、整形修复等更广泛的再生医学领域。
2021年3月,我突发脑溢血。醒来后,我手写了一句“把生长因子打到我身上”。但这个要求过于大胆,并没有成功。我又提出定期抽血,观察生长因子在脑部疾病和神经康复方面有什么作用。
我们的研究发现,生长因子与大脑功能密切相关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,它可能与脑痴呆、抑郁症和癫痫等疾病有密切关系,对此我们仍在深入研究。同时,我们也在利用人工智能,对这些因子与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关系进行运算和分析,希望能设计出更优化的实验方案和策略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前景?
李校堃:人工智能确实给各领域带来了全新革命,尤其在健康领域。我认为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,我们应积极迎接时代挑战,在人工智能与医药健康的交叉领域大胆探索。
传统药物研发过程漫长且复杂,往往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。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,在药物研发的各环节都能实现突破。比如,细胞生长因子在生命体内维持着生命的调控和正常运行。过去,我们对其平衡规律的研究需要很长时间,现在借助人工智能的算力,我们可以快速了解其在人体内的变化规律,精准补充或抑制相关细胞因子,从而更有效地治疗疾病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为了科研,你有“以身试药”的勇气。在当今“内卷”、焦虑的时代背景下,你对年轻人从事科研有什么建议?
李校堃:对科研的探索需要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,盯住一件事,把它做深、做透、做细,甚至在遭受质疑和否定时也要坚持下去。当我们真正热爱某项事业时,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,甚至达到忘我的境界。这种忘我精神正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。
为提取生长因子,我曾在实验室住了两个多月。有一次停电,冰箱里流出的冰水将我从睡梦中惊醒。
我希望年轻人能真正热爱科研,不仅仅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获取学位,还要为了解开生命奥秘,为人类健康找到新方法。在科研过程中,失败是常有的事,但只要坚持不懈,不断尝试,就一定能取得成功。
我认为,一个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、对事业的追求、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其未来成为科学家的重要潜质和基础。急功近利的心态很难成就真正的科学家。科研需要耐心、毅力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。只有那些真正热爱科学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人,才能在科学道路上走得更远。
促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“双赢”
《中国科学报》:多年前,你为何选择到温州医科大学这样一所当时“名不见经传”的地方学校?
李校堃:2004年,我在暨南大学教育部基因组药物工程研究中心担任主任。时任温州医学院(温州医科大学前身)院长瞿佳找到我,想“挖”我到他的学校担任药学院院长。他的一句话说到了我心坎上:“我们温州就是要你做的这种东西,别人不想做的,我们就把它做到极致。”
温州盛产的打火机、纽扣、拉链等小玩意儿,就是把“别人不想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”。当时,生长因子一直不被外界看好,我被这句话打动了,决心来温州把生长因子研究搞好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20余年过去了,你的团队的科研成果对温州医科大学而言有何意义?
李校堃:我刚来温州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时,那里还是一片荒地,路边开着些小作坊,几幢住宅楼挨着垃圾场。如今,学校发展起来,到处生机勃勃。我们在“生长因子”领域的研究既推动了温州医科大学整体学科的发展,也培养了一个优秀的科研团队。
这些年,我们先后发现了22个生长因子家族成员,对多种疾病都有显著效果,研发的新型药剂制品已在国内外皮肤、骨骼、黏膜等创伤治疗中广泛应用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在你和团队的努力下,生长因子研究推动了地方发展。你认为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如何有机结合?
李校堃:我常在讲课时说,美国纽黑文市的精髓就在耶鲁大学,波士顿的发展离不开美国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。我们在眼科和细胞生长因子领域已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,因此我们将生物制药专业、国家实验室、医院和企业紧密结合,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,谋划建设了“中国基因药谷”和“中国眼谷”。学校以“小因子”“小眼球”撬动“大健康”发展,探索出一条具有温医大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。
“中国基因药谷”围绕生长因子研究,先后落地细胞生长因子药物和蛋白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大分子药物与规模化制备全国重点实验室、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三大国家级平台;“中国眼谷”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生态体系,将教育、科技、产业和政府资源整合在一起。在这一生态体系中,各方相互交融,共同发挥新质生产力作用,形成独特的创新动力。
为了进一步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,温州医科大学每两年组织一次高峰会议,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生长因子领域的前沿问题。通过这些举措,学校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,也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,实现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“双赢”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“中国基因药谷”和“中国眼谷”取得了哪些成效,为学校培养人才积累了哪些经验?
李校堃:对企业而言,他们获得了大量有用的人才。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,还能迅速适应企业的实际需求,为其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。
地方政府也非常满意,因为“中国基因药谷”和“中国眼谷”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。这些项目不仅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,还为当地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,提高了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。
医院也从中受益匪浅。“中国基因药谷”和“中国眼谷”为医院带来了大量科研项目。生物医药的发现、实验和市场应用都在医院进行,这不仅提升了医院的科研能力,还让医院在社会中找到更多价值。医院不再仅仅是看病的地方,更是一个科研和创新平台,能为社会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服务。
大学也感受到人才培养的积极变化。通过与企业紧密结合,大学的人才培养更贴近市场需求,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。大学的人才出口越来越大,毕业生越来越受到社会欢迎,这进一步提高了大学的社会声誉和教育质量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2026年将是第三轮“双一流”评选启动的年份,温州医科大学有哪些“冲刺”发力的举措?
李校堃:高水平大学建设不是“百米冲刺”,而是“接力赛”。近年来,学校紧紧围绕“双一流”战略目标,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,明确学科发展重点,以药学和眼视光医学为主攻方向,以高峰学科带动医学技术、生物医学工程、基础医学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护理学等学科协同发展。
当前,学校正处于冲击“双一流”的关键时期,我们积极构建了以登峰学科建设为龙头、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为牵引、以资源高效汇聚与配置为支撑的发展体系,实现一流的人才培养、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、一流的科研创新产出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
一是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,积极探索卓越医师人才“5+3+X”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,优化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衔接机制。建设医工交叉课程群,推进“医学+X”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。二是聚焦人才生态优化,积极发挥“以才引才”“以才聚才”渠道作用,靶向引才,全球揽智,完善人才特区政策,加大拔尖人才引进力度。三是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,实施科技创新攻关行动,以登峰学科(药学)为引领,打造覆盖校本部、直属和非直属附属医院协同发展的完整学科体系,并深化与瓯江实验室、“中国眼谷”、“中国基因药谷”等高能级科创平台融合发展,争取更多的标志性成果转化。
产教融合打破壁垒
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认为地方高校应构建怎样的大学教育模式?
李校堃:什么样的大学教育才是最理想的?我认为,当前非常重要的方向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。这不仅仅是将人才培养与科研结合起来,更是要培养能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人才。
我们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拿到一纸文凭,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真正学到有用的技能,毕业后在社会上做出有意义的事情。
教育不能过于封闭和孤立,不能局限于校园围墙之内。作为校长,我要求老师在授课时不能仅仅为了考试而教学,还要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。不能当外界已经发展到电动汽车时代时,我们还在课堂上讲授柴油机原理,虽然讲得很有味道,但最终会固化学生的思维,让他们与现实脱节。
因此,我们需要打破高校围墙,让教育拥抱社会。我的理念是——如果一名教授对企业没有影响力,如果一所学院对行业没有影响力,其便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,地方高校更是如此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温州医科大学是一所应用型大学,在推动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体化的过程中,你觉得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
李校堃:在从0到1的突破以及从10到100的深化阶段,最难的还是高校与企业、社会之间的协同合作。如何打破传统的体制机制束缚,建立更灵活、有效的合作模式是我们一直探索的问题。这些困难主要集中在校企间的关系处理、人才管理与认定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。
首先,校企之间的关系需要精心协调。比如,如何界定哪些老师属于学校、哪些属于企业,他们的职称晋升和编制问题如何解决?此外,科学家的专利转让也存在一些限制,直接转让可能无法获得股份,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。
其次,新兴技术进入课堂时,传统的教程和课程体系也需要突破。过去,人才的认定相对简单,主要看文章发表数量。而如今却更多涉及产业化难题,如临床配件、二类器件的放大生产等,这些都需要重新评估和认定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:为了解决这些问题,温州医科大学做了哪些探索和优化?
李校堃:我们设立了产教融合学院,这是一个与传统学校、学院有很大不同的创新机构。产教融合学院的核心目标是打破校企间的壁垒,实现产教的深度融合,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,专门解决企业专家的聘任、高校教授到企业兼职等问题,为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新路径。
教师聘任制度方面,与传统学院不同,产教融合学院的教师不仅包括高校教授,还包括企业专家和工程师。后者被聘为兼职教授,参与学院的教学和科研,他们的聘任标准不仅看学术背景,更需注重实际工作经验和行业影响力。
薪酬制度方面,为了吸引和留住企业专家,产教融合学院采用灵活的薪酬制度。企业专家的薪酬不仅包括基本工资,还包括项目绩效和成果转化收益。这种薪酬制度充分考虑了企业专家的实际贡献,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学院工作。
我们鼓励校内教授到企业挂职锻炼,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。在此过程中,我们制定了明确规则,确保教授在企业的工作能得到合理认定和评估。例如,教授的企业工作经历可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参考,在企业取得的成果也可以纳入学校的科研成果体系。
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的这些经验,不仅适用于自身,也能为其他兄弟高校提供借鉴。
| 分享1 |